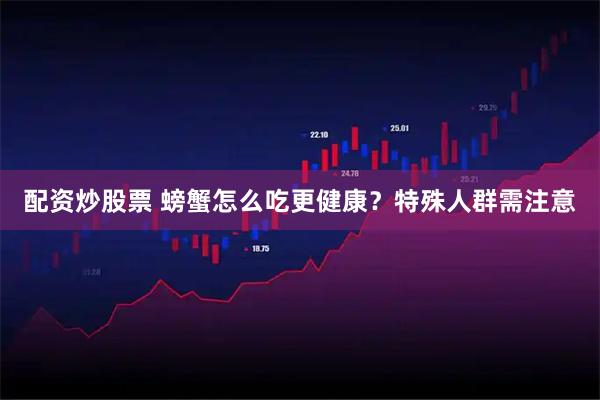《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配资炒股票,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士兵“不怕死”的事例确实不少,甚至到了绝望的时候也不投降。有时还进行自杀式的攻击,并美其名曰“特攻”、“玉碎”!下级对上级的命令,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都要绝对服从,没有一点反抗。难道他们是机器人吗?是没有理智和感情的人吗?

不然,他们同样有血有肉有感情,同样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
1、日军中的私刑
在侵略战争时期,每个青年只要接到征兵入伍的通知,社会上、家庭中都要造成一个为天皇去死、死也光荣的气氛。在打着国旗、吹着乐曲的乡军人会、妇女会、邻里会一长列欢送队伍簇拥下,入伍青年胸戴红花、披着红彩带走在前面,行列中高唱“到海上去,用水渍尸;到山上去,用草裹尸。为天皇而死,绝不回头”的歌,表示有去无回的决心。新兵登上火车时如果向父亲说一句“再见”,父亲便会骂他:“混蛋!在靖国神社见面!”
(靖国神社是祭祀阵亡将士的神庙)强颜苦笑地作出视死如归的姿态。
从这一天开始,一个善良的爱好和平的青年,就要毫无理智地去杀人,去被杀,自己的命运就完全由上级军官决定了。
日本士兵必须绝对服从,这是铁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新兵服从老兵,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和机器人一样不得有丝毫违抗,连挨打的时候也要立正站着不许动,一直到上级打够了以后让你动方能动。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士兵训练得像机器人一样绝对服从,是有“绝招”的。
自从明治建军以来,日本军队内部有一股私人制裁的恶习。
上级有制裁下级的权限,二等兵对新兵有“教育权”,美其名曰“爱的鞭策”,实际上就是私人感情用事,稍不如意就体罚,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为一种习惯,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封建家长式统治。对下级残酷殴打直到半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将校可以制裁士官,士官可以制裁老兵,老兵可以制裁新兵,被打得半死不活也还要保持立正姿势。只许上级一方施加暴力,下级只有服从。这种极为野蛮的行径,后来竟形成一种明文规定,写在《军人敕谕》里。原文是“…应知新任必须服从旧任,下级遵从长官之命即遵从朕命。”
那就是说,下级服从上级就是服从天皇,挨打挨骂是在接受天皇给予的制裁,打人是按天皇的命令进行的,谁胆敢反抗就是反抗天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也没有这种野蛮而公开的私刑。日本陆军和海军继承了这种恶劣传统,把下级管教得伏贴在地是他们的传家宝。

一个新兵一入伍,便要受二等兵的“教育”,稍微不合心意,便随便殴打。及至又来了新兵,他成了二等兵,由“媳妇”成了“婆婆”,便衣钵相传打后来的新兵。如此辗转承传下去。这种逐级施用残酷私刑、绝对不许反抗的制度,让每个士兵见了上级就哆嗦,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直到把日军士兵训练成为毫无人性的野兽,成为完全没有头脑、没有思想,只知绝对服从命令的杀人机器,充满了“武士道精神”。
在这种彻底摧残人性的环境里,军营和监狱一样痛苦难熬。这种法西斯式的“严格训练”,就是日军“不怕死”(其实是不得不死、不敢不死)的奥妙。
这种惨无人道的私刑,上有好者、下尤甚焉,一代传一代,“花样翻新。单就打嘴巴一项,就有许多绝招,有整列嘴巴、往返嘴巴、鞋子嘴巴、皮带嘴巴、对抗嘴巴。就是指排成一排轮着打,打完一排再回过头来依次再打一遍。用手打太累,就用鞋子打,皮带打。再不解气,就让两个该挨打的人互相对着打。这样打还不算完,更厉害的是打完嘴巴以后还要让在地下爬,用棒子打屁股,捅心窝。还有更“妙”的不动手打的办法,如:黄莺跨谷、蝉、骑自行车、举枪、看垒球、各班跑、舐痰孟、舐鞋底、头上顶饭盒等。

用各种花招尽情虐待,残酷刑罚:
黄莺跨谷。就是并排放两张床,从一张床下钻过去再站在另一张床上学莺叫,然后再从这一张床下钻过去站在原来那张床上学莺叫,如此反复。
蝉。就是两手两脚紧紧搂住柱子悬挂起来,连续学蝉叫,什么时候上级说“好了”才能停下。
骑自行车。就是把两张桌子靠近,两臂按着桌子支持身体,两腿像骑自行车一样反复转动。
看垒球。两臂悬挂在枪架上,做出从场外观看垒球赛的样子,连续喊拉拉队的口号。如果坚持不了把脚着地一下,便挨一次暴打,然后再反复去“看垒球”。
各班跑。就是指如果鞋子没有自己整理好的话,就让他嘴里衔着鞋带和鞋,在地上爬着巡回各班,一直到喊停时才停止。
舐痰盂、舐鞋底、顶饭盒等处罚,顾名思义,就不必说了。
接受以上各种私刑时,如果有丝毫反抗或呼叫,或者是带着自我嘲笑或面带痛苦、不甘心的表情,都要被打个半死。周围的人只许观看不许出声,不能有同情怜悯的表情。
军队的私刑不单纯是肉体的折磨,而且是彻底的精神上的侮辱,把新兵身上能够剩下的连最后一点点普通人的自尊心,都要剥夺干净。
在这种精神折磨下磨练出来的日本士兵,挨了打满身是伤也不敢叫喊,让你爬就爬,让你滚就滚,让你立正就得直立不动,绝对不敢违抗。命令你去冲锋,去“玉碎”,就只有立正敬礼以后,乖乖地去送死。
有一位侥幸未死的特攻队员回忆说,为什么有许多青年明明知道有去无回却还要去参加特攻队,去当肉弹勇士呢?原来那是一种事先设计好了的把戏。在兵营里排列好长队,上级军官训过话以后,便命令:“志愿当特攻队的人举手”,或者是“向前一步走”。由于日本兵经常受不堪忍受的苛酷待遇,在淫威之下谁也不敢反抗,便都抢先举手或前进一步,没有原地不动的。

“自愿”只是一种形式,和强制没有两样,只有苦水往肚里咽,还有什么办法!
2、不投降要“玉碎”的秘诀
《战阵训》是日本军队中人手一册的必读小册子。其中命令士兵:“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宁死也不能把阵地交给敌人”,还说:“把生死置之度外是崇高的献身奉公精神,应超越生死,一意为完成任务而迈进。竭尽一切力量,从容为悠久的大义而死,以此为悦。”
根据这段话,长官不顾部下死伤多大都要命令进攻。
这本书支使着日本军队,不管战略对不对,不管上级指挥官的命令是怎样错误,都要冒死去干;什么也不让士兵知道就要他们背着不幸去死。太平洋战争中有四十多万日本海军、二百多万日本陆军战死或饿死,到走投无路时也不许投降,只可自杀或“玉碎”。
日军要求他的官兵身负重伤后,宁可自杀也不能当俘虏。
《战阵训》中说:
“知耻者强,要经常想着家乡和家庭的体面,努力奋斗回答他们的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背罪人的污名。”
如果被放到有死无生的境地,举手投降或者是拒绝执行上级战斗命令躲避战斗的话,那么,军法会议就等待着他。也就是说,定要按抗命罪或敌前逃亡罪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军队在没有接到转移命令以前,必须原地不动,即使全部战死到最后一兵,也不许投降。
1939年5月日苏间曾有过一次诺门罕战役,被俘的日本军人在停战以后被释放回来,马上就被送上特设的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最后交给他一支手枪让他自尽。日本军人明白,一旦参加战争,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投降更是死。只要开赴前线,便很少有生还的可能。

战后,许多在军队服过役的将士在回忆8月15日投降那一天的感想时,都异口同声地说:
“那一天,猛然听到广播中播放投降的消息,我不知道我的耳朵听到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知道是欢喜还是悲伤,茫然若有所失。我各处乱跑,不知东南西北。这一天,我觉得比平常的哪一天都长得多,我真能捡一条命再不用去送死吗?”
让日本人民去死,前方尸山血海,硝烟弥漫。而军国主义侵略元凶东条英机、杉山元、永野修身、畑俊六、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次郎、寺内寿一等人,以及各战地的司令官、作战参谋们,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局长、部长、课长们,这些军国主义集团的上层人物可不愿意死,他们只是躲在东京或各战地防护牢固的司令部或战地指挥所里,用电报电话训令前方将士去死。在前方大批将士战死饿死的时候,他们还有艺妓、慰安妇陪伴着喝酒,《战阵训》中的训令和他们是无关的。
3、灭绝人性残忍至极的屠杀和自杀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集团的各级指挥官,除了无知和愚蠢以外,在灭绝人性、极度残忍这一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他们不但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如草芥,对本国人民也同样草菅人命,所谓“让谁死谁就得去死”,实在是正常的有理智的人干不出来的。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战争中,每一时刻他们都在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战场和后方、外国和本国、陆上和海上、直接和间接,数千万生灵惨遭各式各样的涂炭。
南京大屠杀,东北、华北的万人坑,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新加坡、缅甸、菲律宾的集体大屠杀,拿活人当靶子,吃人肉、杀人竞赛等等都是惨绝人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杀人当作吃饭喝茶,毫无怜恤之意,毫无人的感情。
这些杀人狂把对被侵略被奴役国家人民的残忍手段也同样运用到对付本国人民身上。
塞班岛和提尼安岛都是日本的领土,岛上居住的是日本人民,而军国主义分子居然毫不容情地强令他们去死。除了被迫上阵、死在战场上的以外,对躲到岩洞里、沟壑坑道里的同胞,居然用机关枪大片扫射,可谓“耕庭扫穴”之举。对于最后逃到海岸边的男女老幼,日军竟逼迫他(她)们从悬崖绝壁上跳下自杀!绝壁悬崖上挂满血肉淋漓的尸体,这样的悲惨情景确是亘古未有!
阿图岛、硫磺岛、冲绳岛以及其他岛屿上的军民,战败后日军指挥官都一律命令他们全部去死。最残酷的“发明”是所谓的“特攻队”,让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驾着飞机或乘坐小型潜艇,抱着炸弹或鱼雷硬往敌船上撞,使之与敌同归于尽。

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哪个青年自己,哪个青年的父母兄弟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呢?发明“特攻”的创始人自己难道愿意抱着炸弹去送死吗?不,那位“发明”“神风特攻队”的第十四航空司令官富永恭次大将(大西泷治郎的前任)在“特攻队员”列队出发前曾慷慨激昂地向他们训话,说:“你们将成为军神,我不久也会丢下部队跟着你们去。”
实际上,他的豪言壮语刚讲过,就慌慌忙忙爬上飞机逃到台湾后方基地去了。
英帕尔战役的策划者、发动者和指挥者牟田口中将,七七事变时驻兵在中国丰台,亲自指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他骄傲蛮横达到目空一切的程度,强令三个师团在没有后勤供应的情况下越过高山溪谷向印度英帕尔进攻,说什么“没有粮食向敌人要。”
三个师团在前方弹尽粮绝的时候,他仍强令坚持、不许退却,自己却跑到仰光由艺妓陪伴着饮酒作乐,及至他的败军狼狈溃逃时,留在沿途的只是堆堆白骨!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战后有许多幸存者曾进行过描述,许多记载令人不忍卒读。难道这个地球上还发生过如此荒唐悲惨的事情吗?古代幻想小说中描写的恶魔世界难道变本加厉地成为现实了吗?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原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将,依其亲身经历的体会,把这场战争总结为“魔性战争”,应当说,他的概括是恰如其分的。
4、长街哀求“千人针”
在人们被迫将儿子和丈夫送到前线去死,强忍痛苦把眼泪往肚子里流的时候,无助无告又无望的日本百姓只好天天祈求神灵保佑,用迷信这个鸦片来麻痹自己,来填补内心的哀伤。

战时日本的大街上,排着长队买东西的队伍、奏乐呼口号摇旗呐喊欢送新兵入伍的队伍、迎接阵亡士兵骨灰回来的队伍是天天可以看到的。此外,还有一种最令人不忍目睹的队伍,就是祈求“千人针”的人群。
按迷信的说法,前方的士兵身上如果系上一条由一千人刺绣的白色布带,上面刺有日本国旗和“武运长久”四个字,就可以和神符一样保佑佩带者不死。所以,大街上到处都有悲哀凄凉的妇女手持白布,见到过往妇女就迎面施礼乞求替她刺绣一针,然后毕恭毕敬地鞠躬致谢。
可怜的“千人针”,是为了得到精神的慰藉呢?还是对即将死去的丈夫和儿子的最后一点祝福和期望呢?人们的痛苦埋在心里,辛酸的滋味有谁知道!
根据明治宪法,日本男子年满二十岁就有加入军队服兵役的,义务,但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在校生可以延期到二十六岁。东条英机任首相以后,从1943年9月21日开始停止学生延期入伍。不久,由于最前线下级军官不足,对理工科大学生也开始大量征集,仅1943年一年就征集大学生十三万人。
1943年10月21日,七十七座大学学生出征壮行会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苑体育场举行。观看台上挤满送行的父母和女学生。一位东邦大学的女学生木下和子回忆当年的情景,写道:“我一想到这些人很快就要死去,我的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无意识地挤到观览台最前方,一面流着泪,一面挥着手。”
当时担任乐队指挥的现桐朋学园大学教授荻谷纳回忆说:“我那时不敢说有关战争的话,也不敢想,只是一场心情沉重的演奏。

那些大学生们还没有军装可换,是穿着学生制服的‘陆军二等兵',人们觉得他们就像是被送往屠宰场的牺牲品,是有去无回的可怜的炮灰。”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满盈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